名作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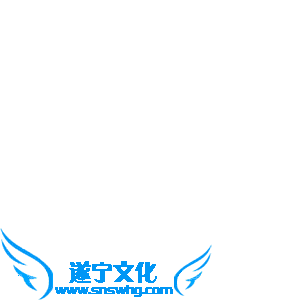
末日黄花
格尼
1
1
1
那张桌子,我们叫“菊花台”,这和颜小菊有关。
桌子摆在红灯笼餐馆门口,只要没客人,颜小菊就坐在那里。她低垂着头,手里一直干活,剥蒜,摘菜,剪干辣椒。哪怕我们忙得脚不沾地,她也干这些活。她还是很不好意思,不管谁看她,还是她看谁,脸都要红。她坐在那,就一直红着脸。实际上,她从刚来那天开始,脸红从未停止。
我们没把她当回事。甚至也没把江师傅当回事。
那天早上,吴老板为节约用油跟厨师吵起来,厨师脾气倔强,舍了两千块钱不要,撒腿走人了。吴老板先把招聘启事挂在门口,又给各个中介公司打电话,最快的都要五天以后来人,要价极高。当天中午,吴老板到厨房应付一阵,累得满头大汗,顾客还退掉好几个菜。有个戴耳机的年轻人指着一盘回锅肉气愤地说:“你们这也叫菜?是不是不想开了?倒给我钱我也不吃。”吴老板只会当老板,不会当厨师。
“狗日的。狗日的。狗日的。”吴老板说。
吴老板不高兴,我们谁也不说话,配菜的王小米破例没有听歌,胖红红也不闹喳喳的了,我们都坐在吧台周围,看屋里屋外那些空荡荡的桌子,听吴老板骂狗日的。
江师傅就是那个下午来的。
那时我们趴在桌上睡着了,包括吴老板。猛听到有个粗重的声音问:“你们要人?”我们都醒了。
江师傅站在过道,背个滚圆的帆布包。他长着方脑袋,双眼间距略宽,双眼皮很大,眼珠不怎么转,看人时死定定的,他就那样死定定盯着吧台。
吴老板当然要人,马上就要,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但吴老板沉得住气,慢慢伸着懒腰,双手摩挲着干燥的面颊。
“做几年了?”吴老板说。
“从小就做这行。”
“拿手菜是啥子?”
“干豇豆回锅肉,萝卜干烧腊肉,灌浆鱼,麦粒扣肉……”江师傅说的这些菜我们菜单上一个也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江师傅他爸是农村厨匠,家里办红白事寿宴的要找他做酒席,江师傅是跟他爸学的。并且他曾在大酒店也做过。
“嗯。先试试吧。”吴老板说。
从吴老板那不经意的语气和痛快程度可以判断,他只想让江师傅先把这个坑填上,没必要过多盘问。只要是厨子,怎么也比他强。
“背包放下嘛,坐吧,坐。”
江师傅却不坐,也不放包,扭过身子说:“还有她,她能干得很!”
我们这才发现帆布包背后还藏着个细脚伶仃的女子,长得细眉细眼,穿着宽松的蓝布裤子,圆领碎花衣裳,一双透明的凉鞋,那鞋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水晶鞋。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尤其是头发,发质粗糙,在背后编成大辫子,再对折用胶圈固定,形成一拃长的环。这人就是颜小菊。江师傅往前挪一步,她跟着挪一点,江师傅到桌边坐下,她也紧挨着坐下,低着头,双腿紧并,蓬松的刘海下,一张脸已是透红。
胖红红附在我耳边悄悄说:“好土哟。”胖红红天生嗓门粗,颜小菊大概听到了,两只脚不安地揉搓,水晶凉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她没穿袜子,脚花里胡哨的,好像沾了灰,又沾过水。
“真的,她能干得很!”江师傅笃定地说。
“我这不缺服务员,她可以到明明小吃部,就在旁边那条街。”
“她没法,离不得我。”
“很近,几步路。”
“她没进过城,我不放心。”
半晌,江师傅叹口气。“谢谢老板了,我再寻寻其他地方。”说着站起身,颜小菊紧跟着站起来。
“你上厕所的功夫都可以跑去看看她。”吴老板说。
江师傅闷头想想说:“不得行,我不放心。”
“你们老家是哪的?”吴老板找话拖住江师傅。
“桥头沟。”
吴老板问我们,我们谁也没听说过桥头沟。
“就是陈家坝那里头。”江师傅说。
我们也不知道陈家坝。
“兴隆镇。”
我们都知道兴隆镇。兴隆镇够偏僻了,再往里,还得往里,那桥头沟大概要与世隔绝了。
“你们是两口子吗?”
“是。哦,还不是。我们出来赚钱,就是想回去修房子结婚。”江师傅羞涩一笑。
“今天要是找不到事情咋办?”
江师傅说他们已经在火车站广场住了两个晚上,找不到的话就再住一个晚上。总会有同时要两个人的饭馆。
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会儿,江师傅把背包往肩上耸耸,哈着腰向我们点点头,默默朝门外走,颜小菊紧跟着。
我们都看吴老板,吴老板的脸拉得老长。待他俩刚要跨出门,吴老板说:“你们都试一下吧。狗日的,真是遇得到。”
他们折身回来,颜小菊抬起头忙低下,脸又红了。那一瞬,我看到她眼里有光亮,不知是明媚还是泪光。江师傅仍是那副神情,一双木呆呆的眼死定定看着吴老板。然后,江师傅朝吴老板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太感谢了!”他说。
我们都清楚,三五天的事,最多白搭几顿闲饭。何况,她还要干活的,生意忙起来,有多少人用多少人。我们都不怎么搭理他俩,几天时间,相处来干什么,他们走出这个门,跟我们就再无交集。我们为这个店焦虑,也为自己的饭碗。王小米,胖红红和我在这个店里干了两三年不等,对店有一些感情了,我和胖红红也像闺蜜一样,整天谈论各自的男朋友。吴老板也对得起我们,从没克扣过工资,有次胖红红忙得不小心摔碎了一摞碗,起码十几只。吴老板一狠心说:“老子倒想扣你点钱,扣了我比你还不好过,算逑,狗日的。”吴老板是对自己狠心。而吴老板留下他们,是动了恻隐之心,顺带解燃眉之急,再不怎么样,总算个厨师吧。否则,这都半下午了,他俩铁定还要蹲一夜火车站。这样,我们守着新厨师,等待另一个新厨师的到来。
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江师傅做的菜极受顾客欢迎,有几位顾客一天来吃了两顿,第二顿是带朋友来的,那朋友是嘴刁之人,连连夸赞,说好久没吃到这原汁原味的东西了。对一个餐馆来说,没什么比厨子手艺好更重要。另外,江师傅干活麻利,踏实,还节约,这节约又是骨子里的,只要能吃的都舍不得扔。比如,红萝卜块,土豆条,白菜老帮,茄子把,这些配菜用剩的边角料统统收进盆子,经江师傅拾掇,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烩菜,成了我们可口的工作餐。
这样的厨子真正打着灯笼难找,吴老板那张绷了三天的圆脸终于舒展开来,到第五天,中介公司找的人过来,吴老板打发走了。好厨子当然得留住,必须留住。
只是,颜小菊有点让人犯愁。
一开始,颜小菊还是跟在江师傅屁股后面。吴老板说:“你这样,他怎么干活?你的工作在前堂。”江师傅在颜小菊耳边嘀咕几句,颜小菊才到前堂。
加上外面两张,餐馆有十二张方桌,吧台背后是两个大包间。颜小菊把所有的桌子椅子全擦了一遍,全擦,意思是桌子腿和椅子腿也擦了,是蹭的。因为那些腿确实够脏,上面腻了一层黑油泥。另外,鱼缸、玻璃门、吧台、墙壁的瓷砖,抹布能到达的地方,都擦了一遍。颜小菊不说话,只闷头干这些事,把红灯笼餐馆收拾得里外光洁一新。也把我们的眼睛都擦亮了。但是,颜小菊不会接待顾客,一说话就脸红,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后来干脆躲在外面不进屋了。来生意时,我和胖红红上阵。生意忙过,颜小菊就上阵。店里客人用的碗筷都交给洗碗公司,不需要自己洗碗,到了第四天,颜小菊没活了。哪个地方也不能白养活人,这点就算颜小菊不知道,江师傅也知道。江师傅把厨房里的零活分给颜小菊,颜小菊就坐在外面一张桌子旁边,面前要么摆个盆,要么一个塑料篮子,手里始终忙活着。如果颜小菊的作用仅是这些,就显得多余。她干的活我们都可以干,也有时间干,她只是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我们愿意,吴老板不愿意。但她就像麦粒扣肉里的麦粒一样,一层层紧紧叠在肉片里,她和江师傅两人是一道完整的菜,分不开的。吴老板当然意识到这一点,要想留着江师傅,必然要收纳颜小菊,权衡一下,利大于弊。况且,颜小菊那么勤快,比胖红红和我都勤快。
“茜茜,你带带她。”吴老板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希望她真能像江师傅说的那样,熟络了就好了。吴老板信赖我,因为我读过大学,尽管大学生遍地,但毕业后到小餐馆打工的毕竟少数,要不是我家住附近,我也不会临时找这么个工作,哪知这一临时,一年就过去了。
我给颜小菊介绍了桌号,和一些简单的待客方法,她跟在我身后,脸上的红晕一波接一波,还没恢复本色,皮肤下的血液再次汇聚,没片刻停止的时候。见过容易脸红的,却没见过红个没完没了的。她还是尽量躲避跟客人接触,只要外面没人,她就坐到桌边,用其他活弥补,一直红着脸。
胖红红经常从那经过,就说:“你到底害羞个啥子嘛!”胖红红把这话说成口头语了,有一天多说了一句:“又不是光胴胴,还怕看?”
就这一句话让她受惊了,从座位上猛弹起来,一阵风似地跑进没人的包间,好久才低头出来。
我们无法理解她的脸红,什么年代了,还一副羞答答的样子,难不成要学习古人,戴一截面纱见人?
还有一件我们无法理解的事。
有一次,王小米出来抽烟,坐在颜小菊常坐的位置。王小米的耳朵上时常戴着耳机听歌,一边跟着唱。颜小菊端一簸箕折耳根出来,看到王小米,就转到另一桌,却并不坐下,背起身子摘折耳根的长须。她的脸又红了。
王小米一根烟没抽完,去上厕所,回来时正碰上颜小菊端着簸箕要往那桌上挪,但王小米不清楚,动作也快,不等颜小菊过来,已经一屁股坐下去了。颜小菊又闹了个大红脸。
胖红红就用肉拳头砸王小米的肩膀:“你还不让开,人家不好意思开腔。”
王小米龇牙咧嘴地说:“那边不是一样吗?”
“没,没得啥。”颜小菊低声说完,端起簸箕匆匆躲厨房去了。
我们这才发现,其实这些天,颜小菊在外面始终坐在那个位置。两边有什么不同呢?经过认真比对,最后发现两张桌子除了台布颜色不一样以外,没什么区别。颜小菊坐的那张是红台布,另一张是黄的。
王小米当时在听周杰伦的《菊花台》,挠挠头,挤着小眼睛说:“难不成这也是菊花台?”
我们哈哈大笑。
1
2
1
我是个爱笑的人,我的笑点很低,胖红红也是,我们每天都在笑。
我们笑颜小菊的菊花台,若有那桌的菜,王小米会在厨房抻起脖子唱着喊:“菊花台,满地伤……上菜!”
有时顾客也会听到。顾客问这桌不是外台1号吗,怎么叫菊花台?
我们笑,顾客也笑。颜小菊红着脸。
我们还笑江师傅。
江师傅对吴老板很尊重,只要吴老板一进厨房,哪怕他正忙,也向吴老板欠欠身子。假如他刚刚忙完,端杯茶坐小板凳上歇息,吴老板在这时进来,他会立即起身,放下茶杯,等吴老板巡视一番出去,他才又坐下。吴老板说:“你不要太客气,大家一家人。”他欠欠身子,还是如此。一天到晚,吃饭、上卫生间和打烊后才走出厨房。他说,这是规矩。他也对王小米这样说,厨房的人不能没事总往外跑。同样,前堂的也不能没事总钻厨房。这是规矩。他循规蹈矩的样子,使我们很想笑。但他似乎太严肃了,脸上有种肃杀之气,好像我们一放声,就成了嘲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偷笑,用眼神传递。
颜小菊时常悄悄打量我们,尤其是我们笑的时候,她会忽然把头低下,红着脸,像是在忍受某种不得不忍受的事,薄薄的嘴唇紧抿,手里的活做得更快了。她动作麻利,这手收了一摞碗,另一只手的抹布已把桌面扫干净了。她两条纤细的小腿奔来跑去,像只活蹦乱跳的小鹿。耳朵也灵,有时我刚一张嘴:“颜……”她已到我跟前。我干脆就直接叫:“菊!”她看着我,眼里有光彩流转。似乎我这样叫她,让她觉得亲切。胖红红就叫她:“颜。”我们都看出来,只要她过了脸红这关,一定是另一个江师傅。看样子,她正在过这关口。
吴老板无意中得俩宝贝,又被工荒闹怕了,担心有闪失。吴老板在一年多时间里,让我们老板娘意外怀孕两次,老板娘既不吃避孕药也不安环,怕发胖,怕脸上长斑。老板娘在家里照顾一个高中生,还带着个三岁娃娃(意外怀孕生下的),一做人流手术,吴老板就忙得焦头烂额。这就是吴老板担心的极容易发生的闪失。所以,自从王小米开始追求胖红红,吴老板就以过来人的身份警觉地对王小米说:“要注意,一定注意,套子那东西最不安全,狗日的。”
吴老板在一天清早把这话说给了江师傅。当时,江师傅戴着厨师高帽站在灶台往一锅热油里放葱段,滋滋啦啦,响个不停。吴老板等江师傅烧好油,趁我们几个女孩子不在,就给江师傅说了。
江师傅习惯性地向吴老板欠欠身子,摇摇头,表示没听懂。
吴老板重复一遍,加了一句:“怀起娃儿就难办。”
江师傅沉默半晌,好像忽然明白了,双手来回揉搓,脸竟一下子红了。
“我们还没。”江师傅嗫嚅着说。
“现在是没,有了就晚了。”
“我们还没结婚。”江师傅说。
“我知道你没结婚,所以才要抓紧避孕,你们是一个藤上的南瓜,怀了娃儿都得回家,还怎么赚钱修房子?我是为你们好。”
江师傅这时严肃起来,说:“我们还没住一起。”
“啥叫没住一起?莫不好意思,我不得干涉,人之常情嘛!只不过这环境糟糕了些。”
“没住。”
“你不会说你们从来没住一起吧?”
“还没结婚,咋住一起?”
王小米和吴老板大笑。吴老板说:“你豁人哟!”
江师傅欠欠身子,神情更为严肃,双眼一眨不眨,笃定地说:“没豁人。”吴老板怔愣片刻,慢慢走向门边,回头笑着说:“那就好。”
王小米把这事说给胖红红,胖红红又说给我,当然是笑着说。显然,我们都不信。
怎能相信?我们大致了解一些江师傅和颜小菊的情况,两人一个村,一起长大,都是初中毕业,青梅竹马。而且结婚证都领了,两家相隔不到十米,天天见面,天天一起玩,难道谁还干涉他们一起睡觉不成?好吧,就算不方便,他们到哪找不到一个僻静地方,随便钻个竹林,多简单的事。现在,胖红红晚上到王小米那住,我回家住,江师傅和颜小菊住店里包间,那么多桌椅,想怎么拼怎么拼,多宽的床都能铺出来。
我们不信。
我们不信,还有个更具力量的理由,这就要说说我们花巷了。
花巷原本是卖花的,后来不知怎么有了两家按摩店,再后来,开了许多家按摩店。从花巷走过,总能看见那些露着白腿的女人坐在门口的长藤椅上,把脸抹得煞白,好像不这样,过路的男人就看不见她们。大概因为花巷窄旧,柳树遮遮掩掩,无论阴晴,一条百十来米的街总处于幽暗中,是幽暗罩着按摩店开了起来,越来越多。到晚上,那些写有“泰式,傣式,刮痧,火罐,按摩”等字样的霓虹招牌爆炸似地不停闪烁,就像女人们不断敞开的怀抱。王小米每次夜里经过都会唱:“来吧来吧来吧,多么逍遥,歌声悠扬,哦深情荡漾……”最后,按摩店的“女人花”们替代了鲜花,花巷还叫花巷,却有了别的意味。花巷不开按摩店的只剩三五家,其中一家就是红灯笼餐馆。花巷的铺面大都挨得近,月月按摩店与我们餐馆一墙之隔,我们的包间窗户和月月按摩店的包间窗户相对,一步之遥,若没有防护栏,胆大的能一脚迈过去。我和胖红红独自带着男朋友在包间过夜时,听到过隔壁传来女人的叫声,让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我们不信,江师傅和颜小菊住进去她们就不叫了,我们不信那声音剌激不了江师傅。
店里生意越发好,回头客大增,吴老板在中午翻了三轮客人那天,不吃饭就跑出去了。我们以为他去买菜,江师傅列了一长串货单,结果一会回来,他叫我到外面,塞给我一个圆瓶,悄悄说:“你给颜小菊讲讲,教她咋吃。我看了,她知道你是大学生,听你的。拜托啊,以防万一,我也是为他们好,也为你们,他们在这,你们少干多少活……我买东西去了,我忙死了,要累死了,操心死了,狗日的。”
那是一瓶避孕药,我握在手里,吴老板的摩托已走远。吴老板真急了。
其实,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相信江师傅的,因他看人那笃定的眼神。我只是不能相信这件事,毕竟这是啥时代啊。我给胖红红悄悄说避孕药的事,胖红红半调侃半认真地问:“你说那两个瓜兮兮的,可不可能真没住一起?”我们相视一笑。
午后,江师傅和王小米去包间休息,我和胖红红来到“菊花台”。
“菊。”我说:“你现在想要孩子吗?”
颜小菊拼命摇头,脸霎时红了。
“哎呀,你莫害羞,我受不了,有啥嘛,都是女的。”胖红红粗声粗气说。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要?”我用胳膊肘碰一下胖红红。
“娃儿?”颜小菊惊讶地说。
“嗯。我们女人呀,不能早生孩子,要结了婚,过几年,看合得来不,合得来再考虑。”说着我把药瓶递过去,笑着说:“吴老板知道你们身上没钱了,免费提供,按照说明书吃,千万别忘了。”
颜小菊疑惑地接过药瓶,大概有点近视,蹙眉端详,接着发出一声锐利的尖叫,像是烫了手,药瓶跌落桌面。她捂上涨红的脸,浓郁的红漫延开来,从指缝外溢,连那双被消毒液泡得泛白的手也要被染红了。
我吓了一跳。我不是被颜小菊一连串的反应吓的,而是那药瓶和桌面碰撞,产生了破碎的声音。桌子表面压着一层玻璃板,下面才是红台布。我明知玻璃的厚度,塑料药瓶不可能对它有任何威胁。但是很奇怪,那声音就像是什么东西裂了,以至于我下意识去察看,玻璃板难道成了薄冰?
“我们还没结婚。”颜小菊的声音从指缝中流出,带着粘稠的鼻音。
胖红红看我,我看胖红红,我们又看颜小菊,我们笑起来。
“你们两口子商量好的哈,说法一样。”胖红红将一条粗腿随意斜插一边,摇晃着脚尖。“告诉你吧,不要娃儿都要吃这药,你不吃,肚里就会结一个小江师傅,只要怀了,吴老板一天都不得留你,你想嘛,哪个老板愿意聘用孕妇,出事咋办?”
“你们都在吃?不吃就会怀?”颜小菊指端露出两个黑漆漆的瞳仁,疑惑地看着我们,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脸上。我能感觉到,她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
我点点头。
“当真?”
“那当然,我们老板娘不吃避孕药,做两次手术,你晓得做手术要花好多钱不?无痛的,一次两三千,你舍得?我可花不起……男人那东西挨到一点都不行。”胖红红说。
颜小菊原本脸色已恢复,此时忽又通红,接着变得煞白,像是受了惊吓。她抓起药瓶,匆匆跑进屋。我们都看见了,她奔跑过程中,愤恨地跺了一下脚。
“我就说她装,你不信。”胖红红撇撇嘴。
我的确不大相信颜小菊会装,别的不说,脸红这种事,岂能装出来?我隐约觉得颜小菊和江师傅,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天晚上打烊后,他们都走了,我刚要走,颜小菊叫住我。这时间,江师傅会在灶台前烧一壶热水泡脚,一边泡脚一边看报纸。
我早就感觉颜小菊想找我说话,更准确一点是谈心,像闺蜜,私语一些女儿家的心事。还在学校时,我有过许多闺蜜,我们不好意思羞涩,那是相当落伍的事,所以我们刚一碰触羞涩,就立即跳开,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羞涩,即使我们不小心羞涩了,也只一瞬,之后,大家对私密毫不遮掩,嘻嘻哈哈。没一个人像颜小菊。真的没有。就好像我们不曾怀春。怀春的颜小菊常独自发呆,淡眉微蹙,发丝拂动,待眼波流转着,忽然地,白皙紧致的脸颊就升起一抹红晕,却不是浓烈的红,而是粉。大咧咧的胖红红也发现了这种不同。胖红红曾悄悄对我说:“你看,她土是土气,长得还蛮舒服。”而且,她的声音有着难以言说的美妙,像雏鸟鸣啾,像溪水流淌,像拨动一根很细的弦。她这样美妙地叫住我:“茜茜姐。”
我回过头,看到她站在门口望着我。
“我不用吃那药吧。”她肯定又疑惑地说。
“怎么呢?”我回身走向她。
“就一次……”
“一次也不行,非常危险。”
“江水说没关系的……”这时她生气了,又有些委屈,咬着嘴唇。“晚上这里有猫,猫一叫,江水就睡不着。他就……”
“猫?”
“很多猫。”
“他就怎么?”
“他就去水管子下冲脑壳……还……哎呀……”她捂上脸。
“你快说,我要走了。”
“茜茜姐……哎呀,江水还往我铺里钻。不过,就一次……”
“一次也不行,我说了的。”
“平常你们没住一起?”我说。
“没结婚怎么住一起?”
“那你们怎么住的?”
“一人一个包间呀!”
我忽然明白了猫是什么,也似乎明白了他们。可以想象,月月按摩店每晚发出的叫声,江师傅果真是受不了,颜小菊却不同意,江师傅只好去水龙头下冲脑袋。我好像听到那些个夜晚哗哗的流水声和女人的叫床声交织在一起。我笑了,哈哈大笑。其实我不想笑,可我一想到那滑稽的场景就难以控制。还有,她竟然说那是猫叫。
“你们每天都笑我们。”她低垂着她的头、肩、眼睑、双手,她站在门口清亮的灯光下,整个低垂着,脸庞散发着莹光,像一尊冰清玉洁的雕像。我忽然感到自己的笑声那样龌龊,我喷出的空气那样浑浊。
“一次也不行。”我收敛了笑,一本正经说。
“江水说没关系的,没那样。我怕他哄我,要是他欺负了我,我妈会骂死我了。”
“哪样?”我追问。
“我也不晓得……他说五秒钟,要不他要憋死了,就挨着了。”
“挨?怎么挨?”我想,难道她一点性常识都没有?
“呵,茜茜姐。”
“他把我箍得紧,我数了五个数,推他下去了,这样会不会怀孕?”她急切地望着我。
“他进去没有?”
“去哪?”她迷茫着,就在一瞬间,她似乎会意了,下意识并拢双腿。“他敢!”她的声音带一股凛冽的寒气。我想起有次吃午饭,我们说笑话,她把碗端到一边去吃,江师傅让我们不要逗她,她是有股拗劲的,惹到不得了。看来她还真是有些个性的。接着,她的思绪似乎在飘荡,呼吸变得混乱急促,她满脸通红,嘴角微微翘起,像是带着某种惬意的笑,却又愠怒着。“烦,他好烦。”她的声音变得酥软了,就像她的身体,软塌塌地靠在门框上。
“你是说你们就抱了五秒钟?”
她用力点头,并会心地看着我。
“那你们以前呢?给我说说以前,他要求过你没?”
“我们拉钩了,要等到那天夜里……”她又难为情了,身子扭向门框,脸埋在臂弯。“要在新房子,新铺,新铺盖,新衣服,新袜子,新鞋,红的,里外都是红的,还要好生洗个澡……我们商量好多回了,要等。”她娇羞的声音微微发颤。
不知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冲击着我,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同时,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何必呢。如果这样,当然不用吃药了。”
“真是这样!”
我才发现我用了假设。“好了,我得走了。”我说。她朝我莞尔一笑。我走向幽暗的花巷,柳叶浓密,一股粘稠的气息裹挟着潮湿的地气,使人呼吸不畅。有女人的笑声传来,还有知了,狠命地叫。我一回头,红灯笼餐馆已被密柳淹没,只透出一丝亮光,我恍然觉得,刚刚是做了一个糊里糊涂的梦。
1
3
1
我们的笑愈发难以控制。
怎么控制呢?只要江师傅和颜小菊同时进入视线,自然而然,我们就想入非非,就想笑,笑本来会相互感染,我们就笑得厉害。有时,王小米跟江师傅说着话,颜小菊如果出现,王小米的话题就立即转向,不管颜小菊是否在场。王小米说:“你哥子,咋个回事哦,还留着块地等别个来垦?”王小米说:“你哥子,五秒钟好干啥,弄了嘛!”王小米说:“你哥子,亏不亏嘛!”王小米说:“你哥子,你哥子……”
起初,一提到这,江师傅严肃的脸就像被绿叶红花点缀了的拼盘,一下鲜活起来。他的厚嘴唇先是慢慢撑开,然后牵动鼻翼,再到眉眼,待整张脸舒展,就发出嗬嗬两声短促的笑。
“不得,不得。”他摇晃着幸福的方脑袋,里面像是装满了丰收的蜜水。
渐渐地,他的脸又严肃起来,假若他正干着活,他会先放下,他还是说:“不得,不得。”再把王小米一直盯着,直到王小米抬起头看他那双眼睛,他才继续干活。他还这样严肃地告诫我们:“你们莫逗她,她性子烈。”
吴老板说:“反正你们各人注意,不要一天呼儿嗨哟的,万一哪天控制不住,给我把药吃上,我是为你们好,一天天,还要操这份心。”
而在男女之事上,颜小菊似乎是一棵营养不良的白菜,忽然接触到肥料,她要把自己缺失的养分补回来。下午,她干着活,会鼓足勇气主动朝我们招手:“茜茜姐,过来坐;红红姐,过来坐。”她红着脸的样子,倒使我们顾及她,不看她的脸,很自然地坐过去,假装她是大方的。我们问她一些关于家里的事,当然还有她和江师傅的事。
“妈妈说了,女娃娃家身子娇贵,不能随便跟男人住一起,不像楔一截木桩桩,楔了就楔了,不想要了再拔出来;女娃娃家,那是一辈子的事,破了就破了,没法补的,千万不能随便。我外婆就是这样给我妈妈说的,我外婆的外婆……”
我们笑她,她又把自己低垂下去说:“你们每天都笑我们。”
逐渐地,她就要悄悄地隐秘地吞吞吐吐地问我们一些关于女人的私密话。比如,处女膜是咋个样子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很疼,到底有多疼,她妈妈说疼得着不住呢,像被捅了一刀,她很害怕。她说这些话时,既神秘又纯真,还真害怕了一样抖抖消瘦的双肩,然后就张着嘴,渴求地望着我们。胖红红受不了,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怎么连这个也不懂,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另外,胖红红和王小米处在热恋期间,两人有时打情骂俏控制不住会悄悄做些亲密动作,只要被颜小菊撞到,她的脸立即通红。红就红了,她还会躲到哪个角落悄悄待一阵才出来,再若无其事干活。谁都看得出来,她那若无其事是假装的。这就让胖红红和王小米尴尬,好像做了什么龌龊事,该躲起来的是他们。
“我给你说,痛个屁。”有一天胖红红粗鲁地拍拍桌子,“我连感觉都没得,你妈妈是吓你。处女膜是个啥东西?就一层薄皮皮,步子迈大了都会破,骑个自行车也会抻破,破了你还以为来月经了,就是骗傻子的东西,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在乎那个。”胖红红拍桌子的手一步步拍到颜小菊跟前,颜小菊往后仰,靠在墙壁,窝进墙角,双手抱着肩膀。
“你吓着她了。”我拽胖红红,胖红红就坐回来,很激越的样子。
“怕啥子,我又没法强奸你,我要有法,我就做了你。”
平时,胖红红也说不出这样的怪话来,不知怎么,颜小菊越是一副无知纯洁的样子,就越使得人想破坏。我们为那两个字尴尬地愣着,颜小菊却笑起来,露出一排细密的白牙,脖子朝前一抻一抻的,像小猫在打喷嚏。
“你还笑,我说强奸,你脸咋个不红?我看你就是装。”胖红红说。
颜小菊的脸就红了。
时值初夏,不冷不热的天,我们对太阳还喜欢着。虽然幽暗的花巷很难晒到太阳,夏季闷热,冬季湿冷。但谁都能看到幽暗之上明亮的天空。而且餐馆门前那棵柳树长歪了脖子,每次出太阳,就有一束光射进来,刚好照在“菊花台”那张通红的桌子上。这时,太阳出来了,瞬间,颜小菊身上红光闪闪,脸却被隔绝在幽暗里。
“喂,小菊,你说老实话,你真是黄花闺女?”胖红红忽然温和地问。
“嗯。”颜小菊认真点头。
“来,你过来,我看看,我一看就晓得是不是。”胖红红朝颜小菊招招手。“把头伸过来。”
颜小菊乖巧地把头伸进那束阳光里。
“我听我奶奶说过,黄花闺女的眉毛长得紧凑,没一根乱长,眉梢也不得翘。”胖红红扶正颜小菊的头,认真地看。
“咋样?”颜小菊问。
“急啥子?心虚?”
“没,没。”
“茜,你来看她眉毛。”胖红红朝我眨眨眼,指着颜小菊的眉头,“看,这里有一根冲天炮。”
我凑过去,发现颜小菊的眉毛像两条纤细的狗尾巴草,那些淡黄的绒毛细密均匀地聚集着,整整齐齐。我还看见她额头上浮着一层轻盈的绒毛,闪着浅金色的光。胖红红朝我眨眼示意,我故作惊讶说:“哎呀,真有一根。”
“不可能”颜小菊皱起眉头说。
“怎么不可能?你们只要亲过嘴,眉毛就会乱长。”胖红红说。
颜小菊有些慌乱,猛把头缩进幽暗里。
“我还没看完呢,我还要看看你的腿有没有缝,同了房的,肯定有缝。”胖红红说着,号召我们把桌子挪到一边。“来吧,来,站进去,走几步。”我知道胖红红开始恶作剧了,平时,她总喜欢折腾王小米,要么扣一个瓜皮在他头上,要么在他背上画一只乌龟,还要假装受伤,用以考验王小米对她是否在意。
颜小菊勇敢地踏进那块阳光,一步步朝前走。她穿着淡蓝色的涤纶裤子,略显紧身,身材纤细的她小屁股却圆鼓鼓的,很翘,阳光从她腿缝里透出来,斜射在暗灰的墙砖上,一抖一抖的。
“看嘛,有缝,你自己看。”胖红红指着墙砖说。
任何人那样走,都夹不住阳光。我笑起来,胖红红终于忍不住,搂着我的脖子,嘎嘎笑得像只高叫的鹅。
颜小菊站在墙角,低垂着头,不声不响。但她的眉眼却高抬着,眼珠滴溜溜转动。我意识到她在看我们的裤裆。然后,我牵动着胖红红沉重的身躯挪向路边,站在柳树下,相互纠缠着。我有些无法承载她的目光,好像我和胖红红各自穿着一条破烂裤子。我们回头,看到她夹紧双腿站在墙角的样子,愈发要笑。
我们虽然笑着,但不那么舒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