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原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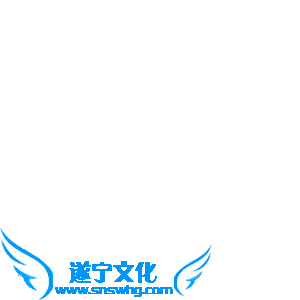
赎罪的村庄
苟子
贰
汪、汪、汪、汪、汪。当何东拼着命顺沟而下,直奔踏水桥累得脚耙手软上气接不上下气的时候,竹林对面那家人阶沿上拴着的大黄狗就蹦跳着咬了起来。他猛地从半晕半醒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我明明是顺沟而下奔踏水桥去的,怎么就整反了,跑到了安子沟沟顶的这个湾来了。
当然,这家人他认得,这条狗他也认得。以往的每一天他从这里过,女主人都要招呼他坐一会儿,这条大黄狗还要摇头摆尾地亲近他。这家人的男主人是个70岁的老头,姓谢,叫谢新岳,是他学木匠手艺跪拜过的师傅。女主人是自己的小师妹谢梅,是谢新岳的幺女,个子矮小,因小时候发高烧得过脑膜炎略有智商障碍,小学只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回家放牛割草了——但她随着年龄的增长,上街买卖东西,用手机给她远在厦门的姐姐发短消息也不成问题。眼下,整条沟就他们三个人了。他们三个人除了退耕还林的地之外,几乎把整条沟的田土耕种完了。师父谢新岳年岁大就干些犁牛打䎬的活,师谢梅妹就干些抛粮下种的轻活。他何东身强体壮,自然就干挑粪上高坡,担粮回粮仓的重活。他们三人两家人,每年每季的收成各家地里的到各家,种别人家地的大致是何东四,师父六。除了特殊情况,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一锅煮一桌吃饭。特殊情况就是何东的老婆和他的败家子儿回来了,谢新岳远嫁厦门的大女儿回来了,他们才分开。
可今天他何东大难临头,他父女俩却连嗽都不咳一个。第一个翻脸的是他们拴在阶沿上的大黄狗,挣断了链子穷凶极恶地想向他扑来。他顺手捡起了一根棍子想打,手臂却轻飘飘的没有力气。他侧身闪进了偏房的牛圈屋,却一个趔趄歪倒在了爬满苍蝇的牛粪坑里——腥臊味腥辣味不由分说地从他的鼻孔里耳洞里钻进了他的胸腔肺腑。他仅虚抓了两下就从牛粪坑里爬了上来,呜呜哇哇乱吐了一通,直到呕吐出一团血丝,心里憋闷的难受劲才舒缓了过来。
他偷偷觑了一眼两边,高大肥硕的水牛就侧卧在他的身边,对他虽没有敌意,但也没有表现出平日的那种友好。他满身牛屎泥浆,蜂子就此没了,他非但没有恼怒,反倒有了点庆幸。
正巧,对面那扇低矮的灶屋门开了。他刚想开口喊师妹,谢梅一眼看到了他,就惊慌失措地将端着一盆脏兮兮的洗锅水劈头盖脸泼了过来,扭转身就大呼小叫地沿着竹林往外跑。
他的心底在无限绝望:我他妈今天肯定是撞到鬼了!
安子沟原本是本辖区出了名的一个集体合作社,土地分到户的人口总数是两百余人。自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始,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能走的,走出去无论干啥能挣到钱的,出去了就没有回来。唯一没有走出去的人不是何东,而是他师傅谢新岳。何东是在他老婆带着儿子去广东一年后去过了一次广东,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派出所撵,做下气力的活挣不到多少钱还要受老板的气,他不顾老婆的再三劝留,就愤懑回了家。之后,老婆还打过无数次电话,说广州深圳木匠搞房屋装修很来钱,他回复说,我一个人种了十几亩庄家,总不会不要吧。谢梅跟她姐去的是厦门,因为她矮小不好找工作,好容易找到家制衣厂,又因她干活连连出错,被老板开除回家。他们两人一个是60后一个80后,外出打工的经历相隔十多年,本不该有什么纠葛,但不晓得老天爷是眷顾两个人可怜,还是故意作弄两个人可恶,让他们殊途同归,有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事。
嗨,你要跑,我总不会喊个没有手爪爪的人来扭你。这时候,何东的潜意识指令他不要再去理论师妹一反常态的问题,该解决的是自己浑身上下恶臭反胃呕吐,找水洗澡的问题。
他弯腰捡起一坨石块,狠狠地砸向汪汪狂叫,一刻也不想放过自己的这条大黄狗。他也不管石块击中了大黄狗的哪个部位,趁它嗷嗷直叫拖着尾巴往竹林外躲闪的刹那间,他冲进了对面的灶屋插上门栓就找水。由于房子是上世纪70年代初建的石柱头瓦房,经过四十余年的烟熏火烤,一关上门就低矮晦暗起来,要不是他熟门熟路,换个人肯定会碰个鼻青脸肿。
水缸里有半缸子水,他的心里就像落水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那样颤动了一下,扭头再看到黑黢黢的灶台上的大铝锅还在冒热烟,揭开居然有大半锅热水,就迫不及待地舀进水桶,再从水缸舀大半锅水屯到灶上,提起水桶到猪圈后面的厕所里,从头到脚一遍一遍地用水瓢舀水冲洗起来……当然,墙洞里嫩绿的香皂盒里摆放着一块粉红色的香皂对他没有丝毫的暗示,他也没有客气,抓过来就在脑袋颈勃浑身上下摸了个遍……一桶水用完,灶上大铝锅里的水也热了,当他如释重负般将自己的浑身上下的每一角落清洗了一遍又一遍,才发现自己没有干净的衣裤——我绝不可以打个光胴胴走出去。
门就在这时候“嘎”地一声被推开,谢新岳和谢梅一人拿扁担一人拿锄头气势汹汹地进来了。
幺妹,怎么不见人了?贼人是不是偷了点东西就跑了?
爸,我亲眼见他进了屋的,多半是躲到屋里那个角落里藏起来了!
谢梅“唰”地扯亮了灯线,大声吼了起来,贼娃子——快跟老子出来——不然,老子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了!
谢新岳异常警觉地说,赶紧把灯关了,贼娃子藏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小心他使用暗器先把我们整到了。
“咔嚓”屋里又恢复了原有的阴暗。
师父幺妹——你们两爷子别大惊小怪的,是我,何东。赶紧帮我找身干净的衣服来。
谢新岳眉头一皱,顺手捡起墙角边的斧头,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经过灶屋来到厕所边,当然没有掀开帘直接进去,而是透过篱壁缝穴,看到赤身裸体的这个男人,脑壳肿得像南瓜,脸上青一块紫一团肿得透亮,大包小眼像蛤蟆,就轻声细语地问,你真是何东何木匠啊?听声音怎么一点也不像?
何东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声音嘶哑与以往有些不同,但不晓得咋个才说得明白,就有些着急起来:师父也,我这是撞鬼了——一斧头把那狗日的砍了,又遭蜂子蛰了,心头慌脑壳都痛炸了,刚才又懵里懵懂拽到你们的牛粪凼凼头——我是你打小抱大的,屁股上黑起这一团胎记,就是我死了化成灰你也认得吧。
此话不假,谢新岳与何东的老汉儿既是老庚又是同拜的一个师傅学手艺,他们还同一年讨婆娘,同一年生了娃儿。何东的老汉儿生出他自然个儿,谢新岳生的是个女,心里自然就稀罕儿,不管是在院子边,还是在生产队屯粮的保管室开会,一见到光溜溜的小何东就要嘟起嘴,在屁股蛋上那块又黑又大的胎记上使劲吹,吹得“嘟嘟”地响。此刻,屋里的光线是通过亮瓦透进来的,房顶上风吹竹动,屋内就忽暗忽明。谢新岳定定地盯了好一会儿才看清那团黑黑的胎记。立马转身喊谢梅,去箱子里把我的衣服裤子拿两件来。
谢梅,人虽矮小,听人指使跑个路却快得很。但在一进一出翻找衣服裤子的几秒钟内心里真就像拨浪打鼓咚咚直跳——本以为他们爷俩会好好亲热一番,要是早晓得会弄出这么个凄惨的样子,就一定要想出千方百计阻止他呀!现如今,他杀人偿了命,自己和老汉儿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大姨妈有两个多快三个月没来了,早就想去镇上的医院检查下,总是被这样事那样事牵绊着,要是真有了,以后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她把找出来的两套衣服裤子双手递给老爸,就在屋外的院坝里转起圈来。看到何东穿戴整齐地走出来,脸肿得青一块紫一块像擂钵,眼睛肿得透亮,眯起好像一条细小的缝穴。
你娃先坐着别动,这个样子走出去哪个见到都害怕。谢新岳目不转睛地盯着何东,疑虑重重,你别太急,慢慢地说,今天到底是咋回事?
我说我杀人了,我把我那个龟儿子何曦给杀了——你们怎么都不相信呀!何东沮丧着一副脸几乎哽咽失声。
我们只听说你那个曦曦儿与几个娃儿妹崽伙起,长期待在城里头,至于在搞啥名堂,我们也不晓得。
他哄到我说,他在开发区的电子厂上班——我信以为真。去年腊月二十三那天,我突然接到城里滨江路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在港上港酒吧头,伙起五个娃儿把另一个娃儿砍了12刀,住进了市医院重症监护室,要我们几个家长拿医药费。我硬掏了十万把他保出来,他一天还是东晃西晃不落屋。
不落屋,你也不至于把他砍了啊?
我这阵心慌,脑壳都快痛憋了。
谢梅说爸,你不要追得那么急。他很可能一大早起来担水兑茅斯,还没吃早饭。我先去跟他冲碗糖开水来,再跟他下碗面。
谢新岳会意地回了女儿一个眼神,说,顺便也把抽抽里的阿莫西宁胶囊和散列痛找出来。
叁
何东的身心状态回归到正常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心不发慌,头上的肿也消退了,但脸上大面积被蜂子蛰过之后,本应留下的那种青一块紫一坨的疤痕——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让它一干二净的。
白天,他像往常一样早出晚归地做农活,夜晚却夜夜做噩梦——不是恶人持刀追杀,就是被警察持枪追撵。
他想第二次报警,甚至还想去公安局自首,又怕真给判死刑——天天晚上,等师妹睡着了,他的内心就翻江倒海,在惧怕和自首两个问题上来回地纠结,每纠结一回心里就懊恼就追悔莫及,真希望警察早点找来,早点做过了断,就是判死刑,也比天天像个癌症晚期的病人那样,在恐惧中期盼着死亡的一步一步逼近强,憋屈煎熬的滋味,真是生不如死。可是,天亮一睁开眼,看到师父和师妹,这些想法就荡然无存了。弑子之后——师父师妹就没有让他再回到他那单家独户的三间屋里头去了,跟他们吃住在一起。晚上,师妹等父亲睡了,就遛进来跟他睡在一起。他很清楚,弑子——本是他自个儿的事,但师父师妹伙同把尸体掩埋到了一个神仙都找不到的地方,这种共同销毁罪证的行为,说明师父师妹非但没那他当外人,而是当自家人了。尤其是这两天师妹呕吐厉害,百分之百怀的是自己的种。每当他慨叹怎么办的时候?师父就一幅淡然的表情,说,别管它,天高皇帝远,拖一天是一天,警察真找上们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们平常干啥仍然干啥,日子照过。
师父对何东说,谢梅已经是你的人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警察不要找来,你是我们的依靠,我要靠你养老送终,更不想小孙孙一出生就没爸爸。谢梅也说,你以前是我哥,现在是我的天和地——如果可以,我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真判了死刑,我也要跟你陪葬!
何东这时候才知道师父师早有打算将师妹托付给自己,也不管他与谢秀芬离不离婚,只要跟师妹有个娃,她无需嫁人,以后就有依靠。
他与师妹的第一次,是去年红五月栽了秧子之后,师父去厦门大师妹家省亲,一耍就是一个多月。师父临行时托付他帮忙照管一下师妹,至少隔一天要去帮忙担一缸水。他满口应了。因为师妹个矮体瘦,要她爬坡上坎去跳水,万一有个闪失,自己良心过不去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没法跟师父交代。
师妹是个温柔恬静的女子,个子虽然矮小,但身材均称面目清秀,还是有几分可人。由于书读得少,人就特别单纯,做啥事就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前几年,常有媒人来打她的主意,都是师父先到镇上的茶馆看了人,在媒人无休止的纠缠之后就坐半个多小时的摩的去看家。师父回来笑嘻嘻地说,娃儿瓜兮兮的不说,房子也是烂垮垮的。这两年,再也没看见有媒人上门来了。
何东自小就爱看《说唐》《说岳》等诸多英雄豪杰的连环画,再大点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的小说,滋生出了他一副忠厚仁义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的个性。17岁高中毕业,补习两年仍没考上,20岁跟师学艺,在方圆十乡八里四处做木工活,招不少姑娘喜欢。22岁那年他在唐家湾做嫁妆,与主人家的二女子谢秀芬一见钟情。在女方父母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何东就让谢秀芬的身体中奖了。何曦的名字是他没文化的爷爷取的,要是知道“祸兮”的含义,打死也不会取这样的名字。
何曦的降临,他们一大家子谁都没有感到有啥不对——稀奇得像个宝,一家人都是争抢着抱来抱去,有啥好吃的,都得跟他留着,无穷尽地讨他的高兴。何曦更他妈奇葩,两三岁的时候就知道把别人家的东西往家拿,把同龄娃儿的玩具占为己有。每每左邻右舍找上门来,一家人不问青红皂白,都同仇敌忾,让人家恨得咬牙切齿不欢而散。之后,此丫就一路疯长,同学们的仨瓜俩枣啦,左邻右舍的鸡蛋鸭蛋啦,凡是能吃的,能变卖成钱的,拿得动搬得走的,都会被他悄然偷走。再后来,就到了镇上的中学读初中,与镇上的几个街娃儿打得火热,吸烟酗酒打架,三天两回就别提了,最让老师校长头痛的是,他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同学。——上厕所时,他尿尿冲解大手同学的屁股,没钱了就找好欺负的同学强行借钱,不借或许人家兜里真的掏不出来,就打得人家鼻青脸肿,满地是血。老师带信喊何东到学校去,校长亲自打电话喊何东去学校领人——何东怕承担高额的经济责任,就一拖再拖没敢去。最后是派出所所长,亲自把人送回到家里来的。何东当时长长输了一口气,因为派出所没有提赔偿医疗费的事,只说了句,你得把自己的娃儿管好,再不收敛,满了十八岁,我们就要法办。何东望着已长得跟自己一样高的孽子,心里真是苦不堪言。这些年来,他娃每每在外惹了事,有人找上门来论理,他都好想好想暴打他狗日的一顿。——黄荆条子砍起还没打在他身上,就被妈、老汉儿吼回去了。他们总说娃儿不惹事是傻包,等长大了他自然就懂事了嘛。现如今他长大了,变本加厉地惹是生非,你们如土为安眼不见心不烦倒好了,那个不要脸的婆娘谢秀芬也是当甩手掌柜,跑广州打工好几年了,娃儿不管不说,钱也不寄一分回来。
二十年来,何东一直想搞懂两件事情。一件就是自己怎么会摊上这个忤逆不孝的孽子,另一件是一见倾心的婆娘谢秀芬,怎么一结婚生了孩子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何东永远都记得十年前老婆去广东临行前的那个夜晚——他们缱倦缠绵了两个回合,激战了三个小时,在浑身都累得散了架的时候说的话。老婆,我舍不得你走。老公,我们村子的憨妹崽出去一个月都要挣一千多块,我也不比她傻,肯定也不会比她挣得少。老公,我们不能在安子沟簸箕这么大块天,穷一辈子呆一辈子?有机会让我们出去闯,就不能失去机会哈。但就家里目前的情况,老的老小的小,我们两个只能出去一个。等我在外面站稳脚跟了,帮你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多一年半载,我们不就又在一起了。
现在看来,这个鬼婆娘说的是唬人哄人的屁话。但在当时,何东是一字不漏地全信了。出去的头一年,她在一家手袋厂做工,是隔三差五要给家里打电话,关顾一下老人和娃儿,一个月要寄一两百块钱回来,后来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就间隔长了,寄钱的次数少,数额也越来越少,再后来给家里的电话没了,寄的钱也没了。过年过节,从村里出去的也有人经常回来,对于谢秀芬在外面做啥子——有的说她在理发店当洗头工,有的说她在按摩店当技师,还有的说她在洗浴中心当领班。在当年,何东不是生气,而是气愤。要不是病病哀哀的父母亲拦住他,他就跑深圳去找她了。酗酒抽闷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他排解忧愁烦闷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老天也没对他有丝毫的仁爱,老母亲砍柴从半崖上摔下来,米汤都灌不进,在床上挺了三天就离世了,父亲担粪上坡淋红苕,粪桶架子断了滚到山水沟里头,中了风,从瘫痪倒床到离世整三年。不光是本村的人说何东好,就是方圆十里认识的何东的人都对他翘大拇指,说别看何木匠老婆不是人,儿子不争气,他却是个爱帮忙的好人,老人在世他伺候得周周到到,老人死了还体体面面地送上了山,是少有的孝子,是大家效仿的榜样。但,何东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人的存在与活着,为的就是过日子,生老病死是人过日子的一个过程。对于父母的离世,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没有怨言。
令何东心里万分纠结万分难受极不坦然的,当然是何曦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被学校开除后,他这个当老汉儿的恼羞成怒了好几天,认为这个东西之所以发展成这样,一是从小被一家大小惯伺有关,二是跟街上那些二流子娃儿伙有关。要想彻底摆脱这些坏娃儿,乡亲相邻的好些人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他送到深圳他妈那儿去打工。
何东永远都忘不了他去找谢秀芬那晚的情形。老乡只把他带到一座霓虹闪烁的名叫帝逸宫的洗浴中心跟前,说,她就在里头,至于她出不出来见你,就不好说了。何东点了点头,等老乡拐个街口不见人影了就走进附近一家理发店,把自己吹得人模狗样的出来,就大摇大摆地登上迷离暧昧的帝逸宫台阶,心里像装了熊心豹子胆似地径直往里走。迎接他的是一排光彩夺目,旗袍开衩至胯部的20几位分不清年龄的女子。他一眼扫过去就看到了里头第一个耳垂下边有个黑痣的就是谢秀芬,只用斜眼盯了一下,就给紧跟在后的服务员说,就是她。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领着他进了包间。四目相对,她看见他就像看见了狰狞恐怖的鬼,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直到门外的两个保安破门而入将何东摁倒在地,她夺慌而出。之后就再也不和何东见面,也不接电话。把儿子何曦交给她是通过一个男主管交涉成功的。令何东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之后,何曦自个从深圳回到了安子沟,人变得又黑又瘦,不像人也不像鬼——手臂上到处都是针眼,时常将那么一钉点白粉倒在锡箔纸上,点燃火用管子往鼻孔里吸。隔三差五就要问何东要钱,何东就三五百地给,直到后来听人说那是吸毒,何东才知道那是个无底洞,填不满,才不给的。谁知道,这家伙不晓得信就与县城一黑老大勾搭上了,长期蜗居在城里不回来了,就是偶尔回来,也是要钱,两爷子自然是吵得不可开交,不欢而散。
肆
警察是在半个月之后才来到安子沟的。
那天,老天下了几颗雨,地下的灰尘都没打湿。何东去跟线家沟那几家留守老汉整秧田去了,正好不在。谢新岳砍了几根竹子坐在阶沿上编撮箕,谢梅在洗衣裳。他们远远都看见了三个穿黑色警服的人,从何东他们那笼茂密的竹林走出,沿着通向他们这条小路匍匐而来。谢新岳对谢梅说,不要怕哈,他们问啥,都说不晓得。
似乎最不待见三位警察到来的是大黄狗,它穷凶极恶地站在院坝边跃跃欲试的样子,真还把他们三人吓倒了,不敢近前。那个胖墩墩矮个子警察是镇上派出所的所长陈高辉,他认得谢新岳,谢新岳也认得他。谢新岳假装没看见,陈高辉就主动招呼起来,谢新岳,把你的狗招呼到嘛,我们到你这里了解点情况。谢新岳就抬头吆喝了一声,大黄,回来!大黄狗就听话地退回到了谢新岳身边人立而坐,双眼极不友好地瞪着站在跟前的这三个人,直到谢新岳进屋端出三根高板凳让他们坐下,大黄狗才收敛了一脸的凶相。
矮胖所长陈高辉指着瘦高个给谢新岳介绍说,这是市公安局的刘警官,指着黑沉沉的中年警察说,这是县公安局的李局长。他也不管谢新岳爷俩听没听,又继续说,他们两位是来找何东的。刚才我们去他家了,关门闭户的,也不晓得何东去哪儿了?
昨天还看到他在担水兑茅厮,我不晓得他今天去哪了!谢新岳手脚娴熟地舞弄着手里的篾条,爱理不理地回答道。
晓不得也没关系。矮胖所长陈高辉歪着脑壳盯着谢木匠那副极不热情的样子,心里明白早些年因为老谢拖欠上交款被他弄到镇派出所去关过,想了想就打开手包撕了半截纸,写个电话号码递给谢新岳,说,老谢,何东回来了你也可以不告诉他,我们来找过他。你直接打我手机说一声就行了。
谢新岳装着腾不开手的样子,仍旧舞弄着他手里的篾条。倒是洗衣服的谢梅扔掉了手里的衣服在身上揩了揩,跑了过来接过了矮胖所长陈高辉写好的电话号码,折了两下揣进了衣兜里。
在这三个警察当中,谢新岳觉得最有心计的就是市公安局这个瘦高个刘警官。他不但围到房子转了一圈,还使劲地盯着谢梅洗衣服的洗槽看。他最担心的是洗槽里有何东的衣服和裤子,被他分辨出来。好在他们没有再啰嗦,就急匆匆地走了。
谢梅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把这事通报给何东,被谢新岳制止了。他说,万一何东的电话被他们监听起来了,麻烦就大了。——都说现在的警察无所不能,我们坚决不帮倒忙。最好就是你这阵就去双江镇街上买两张卡,赶紧送一张到线家沟去,喊他把现在用的这个卡号甩了。今晚上,喊他就住在线家沟,尽可能不要回来,有啥动静,我们晓得通知他。
谢梅抖抖索索晾完衣服,从衣柜里找出了父女两人的身份证,拿了二百块钱往已开始掉皮,早该换的黄色坤包一塞,就心急火燎地出门了。
谢新岳仍旧不紧不慢地编他的撮箕,脑海里却回放起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派出所所长,连民警都还不是,刚当上乡上八大员的陈高辉,带起十几个人组成的计划生育工作队,跑到安子沟来逮自己去做结扎的情景。当时,他还不胖,自己也没这么老。也是这么个时节,他们提前就知道了计划生育工作队要来,就提前把鸡、猪、粮食和值钱的家什藏了起来。他们一家老小也没走远,就藏在坡背后的蛮子洞里,一家大小的五六双眼睛一刻都没松懈,密切注视着房子周围的一举一动。——他们一到首先就将房子包围了起来,见关门闭户没有人,也不喊不问就把门锁砸开了。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为首跳得最凶的那个年轻人叫陈高辉,他居然爬上了房顶,将一大片一大片的瓦陡落了下来。他谢新岳年轻时虽不鲁莽,但也有几分豪气,见这帮不是爹妈生不是爹妈养的人欺负人到了这份上,所有的惧怕的都滚一边去了,拖起一把锄头就不声不响地回来了。他们人多,以为他谢新岳就是一只小鸡那么好逮。他一挥舞起锄把,一下子就撂倒了五六个,有两个还被甩到了岩坎底下喔嚯喧天喊叫起来。其他没有近到跟前的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了,只剩得在屋顶上的那个家伙双腿不停地打闪闪,不敢下来。后来,谢新岳还是没熬过村社两级干部出面做工作——去做了结扎,但将他家的房顶也修好了。
谢梅回来的时候,天刚擦黑。谢新岳刚把夜饭煮好,正在剁牛皮菜拌包谷粉——准备喂猪。
谢梅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就知道煮了腊肉,揭开锅盖刚想挑起来切,就“唰”地一下停电了。他们也搞不清楚,这段时间怎么老是停电,几乎都是在天黑到睡觉前这段时间。当谢梅点燃了蜡烛,谢新岳已摸黑将猪食料倒进槽里了。
烛光微弱得像垂暮的老人,黯然中没有点生机。谢梅将红苕舀得多的那碗饭端给了老爸,说,何东在线家沟活路多,不光是整秧田,还有好几家的田坎去年落暴雨冲垮了,要他帮忙做好,我估计至少也要十天半月。新买的手机卡我已经帮他换上了,原先用那个,我随手就扔到深水凼里了——我原先那个卡也扔了,换上了新买的。喊他有事就打我新买的这个号,还特意嘱咐了句,单线联系。
谢新岳从碗里抬起头来,看着女儿笑了一下,看来你娃还不笨,但我们更得加倍小心,我猜,警察不出两天又要来,多半不是白天是黑了,我们睡觉都要警醒点。一定要记到,不管他们问你啥话,你都说不晓得不清楚。问到我,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伍
可是,三天过去了。非但没见到有警察来,整个安子沟仍是一片死寂。令谢梅奇怪不解的是,大黄狗都没咬一声。吃中午饭的时候,谢梅征求老爸的意见,想喊何东回来洗个澡,换换衣服。谢新岳一脸沉得住气的表情,说,多等几天。谢梅嘟着嘴说,你是谍战剧、侦破片看多了。谢新岳只顾埋头吃饭,对女儿表现出来的不满,没有理睬。
于是,谢梅就开始背着老汉儿偷偷给何东打电话,诉说的都是儿女情长的思念之情。何东关心她更多的是这两天呕吐的反应还大不大,想吃啥就尽量去乡场上买。谢梅说,我想见你,老汉儿又不准。幺妹,我也想你——老汉儿说等两天就等两天嘛,不急的哈。何东在挂电话前还说了句,非常时期,尽量少打电话,能不打就不打——这话还是你跟我送卡来那天叮嘱我的哈。哈哈个屁!谢梅眼角挂着泪花回答的时候,何东已把电话挂了,就用短消息把这话发了过去。
老天至始至终没有眷顾川中这个安子沟,风吹了一夜,黑云压坡顶变了回天,就是没有下颗雨——天旱还在继续。何东不在这个沟里,跑到马溪河去挑水灌秧田的活路,自然就是谢新岳的。煮饭、弄牛皮菜喂猪的活路,自然就是谢梅的。日子在焦躁中又安静地度过了几天,何东就打电话要求回来看看。谢新岳跟谢梅说,我扳起指头掐算了一下,如果今晚再没啥动静,明天是个黄道吉日,明晚就可以回来。
天刚擦黑,又停电了。谢梅事先都做了准备,早早都把猪喂了,等老汉儿回来就吃饭。按常规,老汉儿这会儿就该回来了。以往不回来,多数是遇到人路过说话,这两年路过这个沟就几乎没人了,何东又不在,他会跟哪个说话?于是,她就出门穿过竹林,站在沟中间的坡嘴嘴上四处张望,蓦然看到了何东房子附近有手两只电筒在摇来晃去,惊得冷汗直冒。不多会儿,两只手电筒就过田坎对着自家方向来了。
谢梅没多想,转身就往家跑,见老汉儿已回来站在院坝等她,心里就长出了一口气。有两只电筒从底下上来了。谢梅已紧张到了极点,战战兢兢地说完这句话,一双眼睛巴望着老汉儿快点指示。谢新岳说,别怕,他们问啥你都说晓不得。快点,进屋去把灯点燃。
谢梅进屋就找打火机,找了好一阵子都找不到。摸摸索索半天,在里屋抽屉里找到一个火柴盒——里面仅有3根火柴,又都回了潮,全划拉断了。谢木匠说,我兜里有打火机。
灯一点燃,套着铁链的大黄狗就崩跳着狂咬了起来。谢新岳没有像以往那样喝令大黄不咬,而是仍由两只手电筒的光束在院坝里摇来晃去。
哎,谢木匠!快出来把狗吼到。我是李家大湾的李驼子,来找何东帮我们几家人整下秧母田。谢新岳一听真的是李家大湾的李驼子,就从灶屋里探出头来喝住了大黄,请李驼子二人进屋里坐。李驼子说,往回要找何东做事,电话一打就通,这回打了好几次了都说停机。李驼子说,你们的秧田里的秧苗都长出来了,我们的秧田都还没做,是不是很着急嘛?我们只好跑到他家里来找——他家里冷清清的,像是好几天没开门的样子,就想问问你们,他去哪里了。他回来了,请你帮我们转达一下。谢新岳说,我们也不晓得他去哪里了,等他回来,一定把话带到。李驼子二人连连道谢,没有进屋坐,就走了。
安子沟又回归了安静。谢新岳心里很纠结,到后半夜了也没想好,李驼子找何东做秧母田的事是转告好,还是不转告好。
何东悄悄地回来了。大黄狗没叫一声。门是谢梅起来假装上茅房的时候留下的。他们两人亲热得很小心,生怕弄出啥动静惊扰到老汉儿了。天快亮的时候,何东又悄然离开了。离开的时候,自然也把李驼子他们请他做秧母田的消息带走了。
一晃又是十多天过去了,除了附近村子的三四拨人因打不通何东的电话,来找他整秧母田外,安子沟就出奇特地安静。老天有些眷顾这方土地了,刮了一晚上风,洒了几颗雨,地上的灰尘仍没打湿。谢新岳仍旧过着提心掉胆的日子。但心里更惦念何东——想看看他,想跟他说说话。
何东带着一股酒气回来的时候,半弦月正挂在房背后坡顶最高那颗柏树的尖尖上。他没有顾得上跟师父说话,做的第一件事是挑起水桶去沟底水井担水,来回八趟水缸就满了。谢新岳泡了一盅茶水递给何东,歇歇喝口水。何东说,秧苗都长两寸高了——我不在家,全让你老人家受苦受累了。何东说得哽咽,眼角润润的。谢新岳也眼巴巴地盯了他一眼,说,你娃也没少受累,晒黑了。何东从裤兜里摸出一沓钱,递了上去,说师父,这是这几天收到的活路钱,请收到。谢新岳说,你挣的你自己收捡。何东噗通一声跪下,泪汪汪地说,你是我老汉儿,谢梅已怀孕在身,更多的还要靠你老人家操心照顾。谢梅手捧一叠干净衣裤出来,伸手把钱接过去揣进衣兜里,说,水烧热了,赶紧去洗个澡。
是夜。何东没有进谢梅的房间,而是与师父挤睡在一床。爷俩各睡一头,没完没了无休止地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大多是谢新岳在说,何东隔一阵回应一声。
谢新岳从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说起。谢何两姓人都来自湖北孝感,是把手反捆在后背一个连一个经长江三峡押送来的。当时的安子沟房无片瓦,茅草房一间不剩全化为灰烬,七零八落的无头死尸,暴晒荒野。我们的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伐两尺以上的柏树,赶做棺材,非常虔诚地把他们入土为安。三百多年来,谢何两家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互为联姻,繁衍生息,两家加起来不足10个人的村子,截至到上世纪80年代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时,已超过两百多人。原来的茅草屋,大多数变成了砖瓦房,沟底那一家还盖起了一楼一底的楼房。土地下到户那两年,我们安子沟的谢二娃为争田边土角,把何莽娃挖死了,一个从高峰山下来化缘的老道说,真是糊涂啊——不出二十年,这些田土没人耕没人种——全都会抛荒。当时,我不信,可现在,我们这条沟就我们三个人了,还在种些懒庄稼。天井沟罗岩沟观音岩马边沟方圆五十里,好田好土全抛荒,原来上坡做庄家的路也长满了蒿草,无法进人。真搞不懂那老道的预言就这么准。
师父讲的这些话,何东并不在意,也就没有记心里去。倒是师父后边的这些话句句穿心刺肺。
现在这世道还真他妈奇了怪,好多事都很难用好坏来判断。农民交皇粮纳国税,是盘古王开天辟地几千年来恒古不变的理,现在不但不交,国家还要补贴肥料款补贴退耕还林费。你说它好得很吧,又感觉朝纲乱乱的——男人把婆娘杀了,随便去哪里弄个精神病证明就不抵命,给娘家人十万八万封口费,就能摆平到八年刑;还有个娃儿,30岁了,结婚才三天,房都没同到,开车遭车祸死了,赔的命钱和在城里新买的房子的钱,居然让没有睡到的婆娘分了百分之七十五,活活把妈老汉儿喝农药憋死;还有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老汉儿把忤逆不孝祸害相亲的儿子杀了,放在过去这是备受族人肃然起敬的义举,可现在,这狗屁法律不判无期就判死缓。
天还没亮,何东就被谢梅喊了起来,看到了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那张八仙桌上,一海碗面条正热气腾腾地等着他,就深情地看了谢梅一眼,再一挑筷子,两个荷包蛋就冒了出来,心里倍感温暖。


